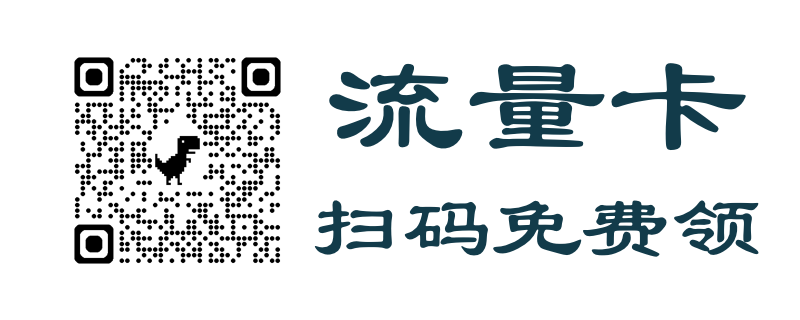序
这是一首羁旅诗,“独在异乡为异客”,孤单寂寞的处境本就容易滋生乡愁,更何况还是在秋雨绵绵的深夜?归思难收,归期无定,归梦不宜,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滞雨”的缘故吗?首句“滞雨长安夜”交代时间地点和缘由。将“滞”字提前,不仅更能体现雨下得久,还能突出夜的漫长,好像是厚实、缠绵的雨连时间的脚步也阻碍了,迟迟不能到黎明。归心似箭,但偏偏又碰上似乎永无休止的连夜雨,给人一种无法排遣的无奈、凝重之感。也为后面的“客愁”、“归梦”蓄势。
“残灯独客愁”描写场景:一盏灯油将尽的孤灯之下,坐着一个满脸愁容的独客。“残灯”,不仅不能给人以光明、温暖的感觉,与外面无尽的雨夜相比,它反而更让人觉得凄凉、忧伤。灯已残,说明独坐已久;独坐久,说明客难眠;客难眠,说明乡愁深。“残灯独客”与前面的“滞雨夜”共同营造出一种朦胧迷离、孤寂凄清的氛围,在这样的意境下,游子很自然会想到自己的故乡。
“故乡云水地”是虚写,是故乡在云水相接的苍茫辽阔之地吗?是故乡有云重水复遥远的阻隔吗?还是故乡根本就不存在于现实,而只在自己如行云流水般飘渺的乡思中吗?这一句体现了诗人特有的朦胧性,怎么理解似乎都可以,怎么理解都给人一种真实而亲切的感受。
“归梦不宜秋”是直抒感慨,语似直切,实则含蓄。雨夜客居,残灯独坐,正是思乡梦回的“好”时候,为什么“不宜秋”呢?因为在诗人眼中,秋就是愁,秋风秋雨秋云秋水……无一不令诗人愁肠百结,在满目愁景的季节,在满怀愁绪的梦中,即使回到故乡,还不是一样愁苦?算了吧,不做归乡梦也罢!其实,这样的梦,在任何季节做都是“不宜”的。诗人在此说“不宜”,其实是“最宜”,有正话反说、不言神伤之妙。
赏析
所谓“滞雨”即因雨而停滞之意,可诗的首句却不说“夜雨滞长安”,反而说“滞雨长安夜”,于是,“雨”也因“滞”字多了几分厚实、缠绵的质感,让人觉得有无法排解的凝重。有雨的夜向来最引人迷醉,最让人动情,因为夜晚、雨水总是让人与怀念结合起来,这怀念因夜而深远,因雨而厚重。更为重要的是,有雨的夜总是为我们创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属于倾听的。无论是“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还是“共眠一柯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无论是“残漏声催秋雨急”,还是“留得枯荷听雨声”,都在显示着一种倾听的力量——对夜雨的倾听,对自我心事的倾听,对更为遥远的情事的倾听。倾听中总是有一个更为久远和辽阔的世界,因为听觉和视觉的不同就在于,视觉指向现在,指向视力可达的存在,而听觉却完全不以时序的意识形式来拥有我们记忆中的全部经验。许多时候,恰恰是因为闭上了眼睛,我们才突破了视觉的有限,拥有了感受的无限。所以夜雨中的凝神寂听会唤醒无数生命的体验,那是记忆,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是我们无法言说的真实与梦幻、记忆与遗忘的重叠。而此刻,对于漂泊异乡、独守孤灯的作者来讲,所有的倾听和回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故乡。于是,在这一刻,秋雨声声为诗人的心灵创造了一个可以缓缓流动,可以无限扩展的空间,这个空间的中心,就是那闪烁着的一盏“残灯”。对于夜来讲,灯光给人的是安宁和温暖,可这安宁和温暖却因为外面的无限黑暗而变得忧伤起来。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正是这小小的一方光明才把世界留在了更加无边的黑暗中。莱布尼森说:“什么是黑暗,那就是最微弱的光明,是最起码的光明。”这句话与其说是在表达光明的无所不在,不如说是在表达有黑暗才有光明,光明因黑暗而存在。所以,这雨夜的残灯中闪耀着的一点温情,变得那么忧伤、那么孤独……
李商隐诗往往在结构上跳跃曲折,暇思无限,有时难免因牵扯得太多、太广泛而显得深奥、晦涩。此诗的前两句却自然平实得多,但在这平实的语言中,精妙的意象的使用创造出深远的易于联想的空间:秋雨、深夜凝听,孤灯、羁旅独坐,一个“愁”字就尽在不言中了。
诗的妙处还在后两句,“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故乡云水地”显示出李诗特有的朦胧而又亲切可感。什么是云水地?是水云相接的苍茫与辽阔?是水重云复的遥远与阻隔?是水流云起的伤逝与叹愁?也许,因听雨而忆故乡,故乡偏也是多雨之地,多雨之秋,故怕归梦也被阻断。也许,越要相忆,越无法忆起,能记的只是那水般葱茏、云般无端的飘渺空虚;也许水流东逝,云卷云舒,让游子倍生时不待我之情,而故乡遥远、归思难收?施补华《岘佣诗话》中说李义山诗“侬丽之中,时带沉郁”,这份沉郁,正是他对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复杂奥妙所作的前所未有的细腻刻划,正是对那心灵深处浩浩荡荡、无涯无际、扑朔迷离之状的传神展示。收句“归梦不宜秋”,语似直切,实则含蓄。夜雨孤灯日,正是思乡客愁时,作者却说“归梦不宜秋”,为什么呢?是因为“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是害怕“浓睡觉来莺语乱,惊残好梦无寻处”?还是担心“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理智的判断阻止不了情感的缠绵,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诗歌贵在含蓄,不宜太露、太直,但造成“含蓄”效果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是“不言”,如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言怀古伤逝,仅写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一事,却道尽了桑田沧海、人世无常之变;有的是“极言”,如李商隐之“相见时难别亦难”,李煜之“春花秋月何时了”,诗语本身明白如话,内心情感一览无余,但因这大白话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使得诗常常超越所描写的情事本身而获得了一种象征意义和不确指性;还有一种在言与不言之间,欲言又止,欲止又言,点而不破,说而不尽。